
数学家张寿武去普林斯顿大学上班的时候,办公室通常会开着门。任何学生都可步入交流。张寿武通常会告诉他们自己眼下在做什么研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只要你解出来,你就超过了我。”
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的博士生张伟会走进来讨论,聊着聊着就岔到了诗词和书法,“聊完之后我才发觉不对,这家伙根本不是来聊数学的。”
当年还会善意提醒 “不要到我办公室里胡说八道”的张寿武,如今谈起得意门生的语调格外轻松而喜悦:“张伟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多了,懂得更多的是刘一峰,数学里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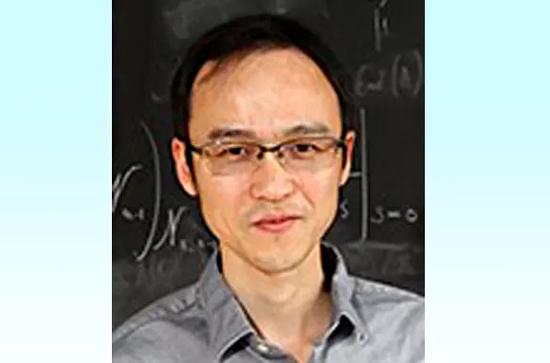
张伟 资料图
毕竟,37岁的张伟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学系教授,33岁的刘一峰则是耶鲁大学的副教授。他们的名字被在拉马努金奖、华人数学最高奖“晨兴数学奖”等荣誉衬托,无疑是国际数学界的耀眼新星。
再加上37岁的伯克利副教授袁新意、2018中科院年度创新人物田野,张寿武的门下蔚然成林。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曾经给出过这样的评价:“带学生,张寿武是欧美数学家中出类拔萃的。”
这些盛放的桃李,悄然实现了张寿武的那一句“超过我”的寄语。张寿武把学生分为三类:“最好的学生把文章做完了,让我签个字就行了;稍微差一点的话,我给个题目,他做出来;最差的是我给的题目他做不出来,我做完之后还要讲给他听。”
在他看来,最好的学生是不应该向老师要题目的。他们不仅是解题高手,甚至是出题高手。那么,老师还有什么可以教给他们?
“成功我是没办法告诉他的,我只能告诉他什么叫失败。我把心里想的、经历过的失败都告诉他,让他不用再经历一次失败。”
“我只能告诉他们什么叫失败”
对优秀学生“放养”式的教育,或许来自于张寿武本人早年的自学和求学经历。从安徽农村走到普林斯顿,这个停留过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等大师的地方,离不开梦想的推动和良师的指引。
从小学四年级读到有关陈景润的报告,数论研究这个梦想就在张寿武的人生中扎根。高考数学失误进入中山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化学系后,他不惜装色盲以转入数学系。张寿武对代数的兴趣引起了一位同样想钻研代数的老师的注意,邀请他开讨论班,与教授们一起学习。
考取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生后,张寿武继续自由地钻研,导师王元院士“是一个极为开明的老师。”“他本身研究解析数论,是个大专家,居然允许自己的学生完全不做自己的东西,放在今天,他的这种度量、这种气派也是很了不起的。”张寿武如此注释王元的“开明”。
随着年龄渐长,张寿武不自觉地开始从探索者切换为传播者的角色。他把这份自由度和交流度转播了下去。 “我的学生,包括做毕业论文的本科生,每星期可以跟我聊一个小时,所以他学的知识全是活的。”
张寿武觉得自己的性格占到了一部分因素:“我不算能很会教别人,但我喜欢跟不同的人相处。”
“我本就是乡下人,各种水平和层次的人我都接触过。不管跟什么人聊天,我都能很快理解对方的想法。而且能顺着别人的想法去转,绝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别人身上。”
尤其是张寿武口中那一类不需要等着老师出题的学生,“你说我能教他什么?我自己都搞不懂我要怎么教他?但我愿意花时间跟他讨论。”
“成功我是没办法告诉他的,我只能告诉他什么叫失败。我把心里想的、经历过的失败都告诉他,让他不用再经历一次失败。”
“我们的问题是,怎么帮助最好的学生?”
与此同时,张寿武觉得在数学教育中,老师这一份作用不可或缺,有四两拨千斤之效。目前师资力量不足,正是掣肘中国从数学大国走向数学强国的关键问题。
他相信,数学是和人的关系尤为紧密的学问,“教数学也一定要通过人去教,不能通过教学大纲,不能简单粗暴。”
近几年来,一批在世纪之交进入北大数学系学习的年轻人逐渐在世界顶级学术舞台上证明了自己,被外界评价为“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其中,就包括北大00级的张伟和袁新意。
张寿武也曾好奇去探究群星涌现的原因,“这是他们自发的,一个班里这么多人愿意做同样一件事情,互帮互助。我也问过他们,会有很多巧合在里面,如果去问北大的教授们,我觉得他们也搞不清楚。”
不过,据张寿武所知,起码有一位年轻老师在促成“黄金一代”抱团学习时发挥了作用。“他们当时有位老师叫杨磊,现在还是北大的副教授。这个人很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聊天。老师愿意和学生在一起聊天、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学生,我想这对学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教书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但光教知识其实是不够的。”
张伟等人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描绘过一副19世纪欧洲沙龙般的简笔画:“北大数学系当时是年轻的老师杨磊教数学分析,每个星期两次课,外加两个小时习题课。题做完之后,他就开始聊数学历史,包括正活跃的朗兰兹纲领。他数学思想独立,不受体系影响,喜欢谈大数学家,比如格罗滕迪克、安德鲁怀尔斯、皮埃尔德利涅这些人,他的激情对这几个数学好的学生影响很大。”
在本科生仅有70人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30多位数学教授同样可以实践这幅生动而浪漫的图景。但在每年迎来几百名新生的中国大学数学系,哪怕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学校都深负压力。
“国内有些教授教一门课,上课的人有四五十人。我觉得他们把课教完,作业改好就差不多了,让每个学生享有每周一小时的办公室交流是不可能的,连硕士生都做不到。”
这是中国高校在数学研究文化上捉襟见肘的真实写照。培养技能,而非培养思想;学生特多,而研究型老师特少。
据张寿武这么多年来对国内数学系的观察,师资力量的问题虽然已经暴露出来,得到重视,但进步的过程漫漫。即使是清华办丘成桐班、基础科学班,将好苗子汇集在一处,资源和普林斯顿、哈佛等世界顶尖高校相比,仍有明显的距离。
“中国的大课要比美国上的好,课程设置严格,要求具体详细,我们的问题是怎么帮助最好的学生。”张寿武说道。“他们很聪明,什么都学得懂,这就要看老师的水平,不能靠教学大纲。”
“我们国家能用最少的资源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想要用最少的资源培养出高尖端的人才,我想这不现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顶尖学生还是要送出去培育,慢慢等国内大学出现一大批顶尖的数学家。”
“带他们走进21世纪的数学”
“我这一辈子,有那么多人帮助过我,我要回馈给国家和社会。中国那么大,想学数学的人那么多。我想给那些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一个机会。”